最熟识的陌生人:快递员和他的很多个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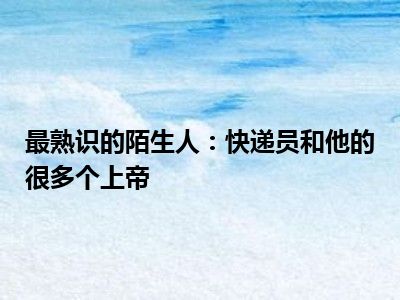
骆易/文 “时薪30元的送货机器”
每一天,中国有超过3.5亿个包裹在送往全国各地的途中。中国快递业的日均处理量已超过7亿件,连续十年位居全球第一。在2024年的前两个月,中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了约23.7%,业务收入同比增长了约13.5%。这些令人瞩目的数据背后,是490万快递从业人员的辛勤工作。
胡安焉在北京担任快递员的时间从2018年4月一直持续到2019年11月。在那个时期,他可能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畅销书作者,书名为《我在北京送快递》。这份快递员的工作,实际上是胡安的第18份职业。在此之前,他的工作经历丰富多彩,包括在物流公司拣货、在酒店担任服务生、在加油站工作、在快餐连锁店和熟食店任职,甚至涉足漫画界,做过漫画社学徒和动漫资讯杂志的美编。这些工作,有的只持续了几个月,最长的一份工作长达两年半。
在做过的这些工作中,他曾认为拣货员是最辛苦的。在物流公司夜间拣货的那一年,他需要每天日夜颠倒上十二个小时夜班,整夜搬运货物,期间不能进食。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使他的情绪控制力明显下降,反应变得迟钝,记忆力也有所衰退。然而,当胡安转行成为快递员后,他发现自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竟然不再感到辛苦。他形容自己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彻底变成了“一个时薪30元的送货机器”,达不到额定产出值就“恼羞成怒、气急败坏”。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的张杨波教授曾经深入1998年华中地区某城市的基层快递站点进行田野调查。他注意到,无论是物流管理科学中注重改进物流网络技术的思路,还是经济学中致力于创新快递配送模式的分析框架,抑或是社会学中对劳动过程的深入理论探讨,每种视角都有其独到之处和局限性。这些视角均未能独立提供一个全面的答案来解释:在快递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快递员是如何执行任务的?在收派快件的过程中,又隐藏着怎样的运作机制?更进一步,面对正式制度的约束和不确定的风险,行动者是如何有效地完成他们的任务的?
与胡安焉在同一地区工作和居住的快递员和送餐员,如果工资不包含食宿,他们的平均月薪大约是7000元。如果收入低于这个水平,劳动力可能会流向其他地区或转向其他职业。实际上,北京的生活成本和工作强度决定了这一市场行情的形成。按照每月26个工作日来计算,快递员的月薪7000元相当于每天270元。在他们每天11小时的工作时间内,1小时用于到达站点卸货、分拣和装车,另1小时用于前往各个小区的路上。除去这2小时的“固定成本”,在剩余用于派送的9小时内,胡安焉计算出他每小时必须产生30元的收入,平均每分钟0.5元——这就是他的时间成本。他每派送一个快件平均收入2元,换句话说,为了不亏损,他派送每个快件的时间不能超过4分钟,否则他可能需要考虑换工作了。
胡安焉不得不从纯粹的经济角度、用成本的眼光来看待时间。因为每分钟值0.5元,所以哪怕公厕免费,花费两分钟小便的成本也得算作是1元;吃一顿午饭要花二十分钟,换算为时间成本就是10元,一份盖浇饭的价格是15元,加起来就是25元,“这对我来说太奢侈了!”。他作为快递员的“理性”选择,只能是经常不吃午饭,也尽量少喝水以减少上厕所。
但这份工作还有更多他作为快递员不能控制的情况,特别是“工作日的白天约有一半的住宅没人”。快递员即使只花一分钟打个电话,支出了0.1元的话费,却付出了0.5元的时间成本;假如收件人要求把快件放去快递柜,快递员付出的时间成本更多,往快递柜里放一个快件平均又要向快递员收取0.4元,“这笔买卖我就亏本了”。如果收件人要求改天再送到家里,快递员的亏损将会更多——额外的话费成本、通话时间成本以及双倍的劳动时间。
更为不顺利的情形是,假如电话没人接听,白白等待一分钟,就相当于浪费了0.5元。有的电话打通后还很难挂掉,客户百折不挠地提出各种难以满足的要求,打完电话后花去的时间成本已经超过了派件费,但快件还根本没派送出去。
胡安焉认为,没有人会发自内心地喜欢送快递。只有在发工资的时候,而不是在客户露出感激的表情或口头表达谢意的时候,“我才会感觉自己付出的劳动值得”。以至于当客户批评抱怨“你这样干活儿真不像话,顾客就是上帝,难道你不懂吗?”胡安焉会本能地为自己辩解:“可是上帝应该只有一个,我每天却要伺候很多个啊。”
“深海里的鱼都是瞎子,
沙漠里的动物都很耐渴”
张杨波在《熟悉的陌生人》一书里采用了隐没关系的写作方法,一个个“面部模糊的快递员”被呈现出来。他梳理出了快递员的各种理想型特征,比如“理性但又不失温情,讲原则但又不失灵活,会合理规划路线,会根据与客户的熟悉程度来适当软化服务合同,在快件破损、快件派送延迟或快件丢失的情况下与客户尽快协商和解等”。
快递员的现实生活与他们的理想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实际操作中,与客户的协商往往充满挑战,而赔偿问题对快递员来说几乎成了常态。例如,有一位快递小哥在小区内驾驶三轮车过快,为了避让一位孕妇而导致车辆侧翻,虽然孕妇没有受伤,但受到了不小的惊吓。为了修理损坏的前挡风罩并进行赔偿,这位快递小哥不得不支付了近2000元的费用,这件事也让他立刻决定辞职,“所受的惊吓可能并不比那位孕妇小”。
胡安焉还听说过一个金额巨大且颇为离奇的赔偿案例:一名快递员在将快件塞入消防栓时不慎损坏了水管接头,导致水喷涌而出,灌入了电梯井内,造成了电机损坏,最终不得不赔偿了三万元。因此,快递员们在私下里常常自嘲:“多干多赔,少干少赔,不干不赔”。
还有一位快递员,有天在路上被后面一辆奥迪轿车的司机拼命摁喇叭给惹毛了,于是摸出一根铁棍,把奥迪车前盖和挡风玻璃完全砸烂,“据说后来蹲牢房去了,因为他赔不起,可能也不想赔”。胡安焉回想起来,自己也曾不止一次有过近似的冲动,“就像一根钢缆绷断后疯狂地反弹,不顾一切地反噬身后的压力,发泄对世界的不满”。
快递员和同事之间也存在着零和博弈——“要么你好,要么我好,不可能大家都好”。每件快件的配送费是划一的,但有的小区好送,有的小区不好送。组里的新人都从最难送的小区送起,刚来的时候不大计较,但会逐渐察觉到其中的不公。所有人只能排队,大家都在熬。假如迟迟没有改善,有人就会离开。最后得到好送小区的人会一直留下来,不好送的小区就让新人去送,“于是小组里总有一半的人雷打不动,另一半的人却换个不停”。
而快递员与网店、与公司之间,也存在着利益的不一致甚至冲突。胡安焉在北京加入的第一家快递公司,在外人眼中口碑很好,堪称“快递界的海底捞”。不过,这种优质服务建立在高成本、高收费的基础上。主管经常要求员工在派件时主动提出帮客户把垃圾带走,还要请客户打五星好评,再在网店里按照好评数排名进行奖惩。
除了早会,快递员每周还要强制参加两三次长达一两个小时的晚会,“没有补贴、福利,只是挨训”,结束通常要到晚上十一二点。客服在客户申诉时多数会处罚快递员。这种种超纲的严格要求和“我不认同但不得不接受的不公平、不友好、非人性的规则和条件”,都让性格内向的胡安焉感到难以适应。
胡安焉发现,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所处的环境,而不是由所谓人的本性决定的,“就像深海里的鱼都是瞎子、沙漠里的动物都很耐渴一样”。他在北京加入的第二家快递公司在2019年底结束业务,全国四万多名快递员全部被遣散。在最后那段日子,因为来自工作的压力全部消失、干活时也不再心急火燎,胡安焉开始用一种不带目的性的全新角度去看待这份工作。“事实证明,只要我不在乎自己的工作效率,也就是说不计较付出回报比的话,那么几乎所有客户都很好相处,都懂得对我绽放真心的笑容”。相对应地,胡安焉也发现自己的大多数感受都变得更加积极、正面、美好,自己也变得更温和、更平实、更有耐心。这或许说明当被迫工作时,“我很容易烦躁、怨恨、满腹牢骚,而且总是不公正地把我每天伺候的客户看得比真实的他们更自私自利、蛮不讲理和贪得无厌”。
当胡安焉发了一条仅客户可见的微信朋友圈道别时,很多顾客留言称赞他的服务态度、感谢他此前的付出。其中一位顾客说:“你是我见过的快递员里最认真负责的。”于是,他想可以用一句并没有夸大其词的话来总结这段在北京送快递的经历:我曾经做得比一些客户见过的所有快递员都好。
“最后一公里”
“没有什么好送不好送的区域,只要客户接电话都好送”“快递员最害怕的就是客户不接电话,没接电话,我是走不敢走,但又不能死等”“派送快件尽量不走回头路,你不要刚走开又有人来寄”“刚才做这个快件就20分钟,你说怎么高兴得起来?”……张杨波在田野调查中收集到的这些快递员的反馈,与胡安焉所讲述的个体经验与个人感受,并无二致。
与快递业内部竞争异常激烈、一线快递员每天收派快件负荷重、快递公司制定的文明分拣制度往往流于形式等三大难题相比,跑好快递的“最后一公里”,其实这才是目前对各快递公司来说最为紧迫的任务——由于客户位置的不确定和派送路况的复杂多变,“最后一公里”成为快件收派最难的一段。
目前,快递公司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已经在大中城市居民聚居区大面积推广智能快递柜自提模式,以有效避免快递员和客户交接快递的时间差。但从经济学角度看,智能快递柜自提的落地,需要充分考虑当地客户的分布状况、集中度和该区域的快件业务量,并不能在任何地区都简单复制推广。另一方面,如果需要持续发展快递服务末端创新配送模式,快递柜运营盈利模式必须从过去以快递员收费为主、广告收入为辅,逐步转向发展社区服务平台和向上集成。此外,建立在快件交接电子化和全方位监控基础上的菜鸟驿站,已经成为对接各个快递公司快件派送“最后100米”的重要接口,实现了派送末梢联结,也提供了另一种解决方案。
在张杨波看来,在科技之外,快递员通过在所属区域内与客户长期交往而产生的“熟人关系”,是破解“最后一公里”收派难题的关键词。快递员收派快件时,面临着正式服务合同和现实条件的双重约束。快递员不得不发展出常规路径、例外路径和循环路径三种模式以优化路径,并往往通过建立非正式关系、熟人关系等方式,对正式服务合同相关条款进行适当软化,在正式收取环节将一部分快递劳动委托给客户来完成,以实现随机应变、优化流程、提升效率、降低成本、规避风险。张杨波把快递员的这种行为称为“服务合同约束软化”,也就是丙方(快递员)在实际操作中改变了与甲方(快递公司)的正式服务合同,和乙方(客户)达成新的合约安排。
在理想的、条件完备的情形下,客户相对集中且确定在场,但现实条件往往不完备——客户相对分散且不确定在场。在条件完备的情形下,快递员可以采取正式派送的形式(当面交付快件并完成客户面签),这样做既保证了派送时效,又控制了派送风险;在条件不完备的情形下,快递员如果遵照合同规定就送不完快件,这促使他们发展出逆向派送(客户到某个指定位置找快递员取件)、虚化派送(客户事后到自己指定的物业、门卫等安全位置取件)、托管派送(快递员通过向驿站、便利店等第三方直接让利合作使其协助保管并/或派送快件)和代管派送(快递员通过向第三方间接让利使其帮忙送快件,第三方因为不获得提成从而不承担快件丢失的责任)。
后四种派送模式克服了客户不在场的难题,而且快递员和客户间形成的熟人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化解快件派送延迟、快件破损或丢失等风险带来的客户投诉。与此类似,当客户不在场时,快递员不得不发展出逆向收取、虚化收取、代管收取和托管收取等四种收取快件的模式。快递员和客户间的熟人关系,既可以通过与客户达成默契来转让填单、打包、在线支付等一部分劳动让客户完成,又可以在实名认证和开箱查验时有效减少因沟通不畅可能带来的客户投诉。“熟人”这个关键词帮助我们解答了更多的问题。例如,对于“为什么离职的快递员大多为资历浅的员工?”这个问题,胡安焉“要么你好,要么我好”的回答事实上源于零和博弈的演化均衡视角,而张杨波则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新手在入职几个月以后,如果做不到“熟路”“熟人”“熟物”,就意味着他还没有完全摸索到收派快件的窍门,尚未学会在客户默许下适当软化服务合同,依然按照正式规定来收派快件,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无法随着学习曲线而不断降低,收入没有起色,离职在所难免。
和时间赛跑的机器人
“快递员对时间的敏感度要远远超过大部分客户……1分钟对快递员来说可能就是5分钟的感受。不少客户在与快递员打交道时会有一种这样的体验:明明才是几分钟的事情,但是快递员却说等了很久。”张杨波在书中对快递员们的时间概念的总结,和胡安焉的亲身体验不谋而合。
在中国,以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为主要群体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近21%。新就业形态准入门槛低、工作灵活性和自主性高,但根据交通运输部、国家邮政局等部门设立的“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的相关制度机制基本健全”的主目标,我们在利益分配、劳动报酬、社会保险、作业环境、企业主责、规范管理、网络稳定、职业发展等方面还有不少工作与任务要完成。就像胡安焉所写:“为了实现整体利益的增长,总有一些人要暂时放弃尊严和权利。”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三十多年来全球经济新增就业的60%-75%来自不稳定的、非正规的、脆弱的就业和零工经济。在未来十年,脆弱就业和零工经济群体预计还将以超过14%的年均增速不断扩大。当劳动占美国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不断降至大萧条后最低水平(58%),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在持续下降,这意味着他们在技能范围内的工作选择变得更少,不得不在低技能工作上恶性竞争。
如何在恶性竞争中争分夺秒地抢夺时间?大企业通过技术和算法的种种规划,让这些劳动者近乎成为机器系统的一部分。
以亚马逊为例,这家电子商务巨头目前已在全球仓库和配送网络中部署了超过75万台机器人,而且这个数目每天还会增加约一千台。当仓库墙上写着“努力工作、享受乐趣、创造历史”的标语时,亚马逊工人的每一步移动都会被传感器追踪,订单路线会被算法系统重新规划优化。吊诡的是,科技创新依然不能让亚马逊摆脱灵活多变的人类劳动力,“技术很重要,但不是万能的,仓库的体力活、重复性工作还是需要大批工人去完成”。而筋疲力尽的工人只能选择在全年促销高峰的“黑色星期五”,发起“我们不是机器人”的抗议活动。
困在算法里的不只是亚马逊的一线工人们,经理们也处处受制约。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亚马逊仓库管理人员有时只不过是“躲在电脑后面的一张脸”。俄勒冈仓库的一位经理抱怨自己几乎没有“休息”这个选项——在12小时的轮班后,他偶尔会在车里先打个盹,免得回家路上困得开不了车。
工作自主性指的是劳动者有权控制自己的时间和活动,包括谁来决定工作节奏、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以及谁对承担的工作保持酌情决定权,但这有可能让他们存在“自由的错觉”。在研究欧洲的外卖骑手时,莱斯特大学教授菲比·穆尔和艾塞克斯大学高级讲师杰米·伍德科克发现,应用程序通过管理订单和预计配送时间,对劳动过程实施精细化控制,并有意把骑手的酌情决定权降至最低,好让骑手成为随时能被替换的螺丝钉。有趣的是,同为灵活劳动者,有的外卖骑手却认为自己“只是平台追踪的一个点”,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反倒很怀念早年在快递服务业工作时的某种社交亲密感:“在许多快递公司的工作经历告诉我,人际关系极其重要。”
眼花缭乱的时代变迁、高歌猛进的技术进步、遍布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竞争逻辑,放置在个体、群体和世代身上的压力都是不均等、不平衡的。当我们目睹快递员与客户周旋、与公司谈判、与资本纠缠、与算法共存、与效率搏斗、与生活和解,却有可能忘记了被系统倾轧的还有我们,忘记了工作只应是生存的手段,而不该成为人生的目的:“所谓的自由,实际上在于你能意识到什么,而不在于你享有什么。”














